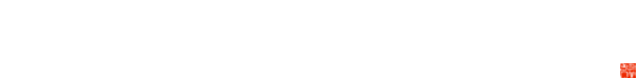金陵的秋,总是先由桂花报信的。
南大仙林校区的桂花似有书生意气,不肯一朵一朵地开,偏要一夜之间忽现千簇万朵,直教人猝不及防。
还记得三年前九月的某一天,那日黄昏时分,细雨飘洒。直到天黑,空气中依旧浮着水汽。师门微信群里忽然弹出导师发的消息:“都出来走走,今天我们在校园里‘赏秋’,谈谈学术,聊聊生活。”我们三三两两地从图书馆或宿舍走出来,迅速聚成一团。
师门素有同游论道的雅习。玄武湖畔的烟柳画桥、紫金山间的梧桐深径、落日余晖笼罩下的羊山湖公园,都曾留下我们谈天说地的身影。唯独在自家校园里这般漫步闲谈,倒是第一回。
导师走在学生中间,黑夹克的肩头微微濡湿。他不时停下脚步,等后面的学生跟上。他的眼镜片上沾着细小的水珠,倒映出路灯暖黄的光。师兄师姐们围着他,像众星捧月,却又比月亮更亲切几分。
行至某条幽静的步道,导师忽然停下脚步,深深地吸一口气,笑道:“桂花开了!”
我们学着导师吸气,果然,桂香沁人心脾,格外醒神。
这时,我们才注意到,昨夜被秋雨打落的桂花隐藏在落叶的间隙,如同撒落一地的碎金箔。秋风只轻轻一扫,地上桂花便都往路边挤了挤——湿漉漉的、温润的、清香的。偶然一阵风,粒粒桂花便离了树梢,随风飘转,有的沾在师姐的发梢,有的落在师兄的衣襟。一抬头,树上的花簇还多着呢,轻轻摇晃着,仿佛在偷笑着回应秋风。
那时候,我是师门年级最低的师妹。那时的我尚缺乏对未来的规划,索性便将迷茫按下不提,只顾拉着师姐的衣袖,絮絮叨叨分享自己在校园内外、南京城里遇到的一切惊喜,连前些日子在老门东尝到的一块梅花糕,都要凑在师姐耳边细细说上三遍。
导师问起师兄论文的进展,言语间并无催促之意,眼神中满是信任。
导师又问及师姐求职可还顺遂。师姐紧蹙眉头,许久未答,也许是怕说得重了导师会担心,只是轻轻叹气,说道:“如今毕业生求职市场的竞争很大”。导师心中了然,让她放宽心,最好的、最适合她的职位正在未来等着她。
待一一问过众人近况,导师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,问我近期是否还常依赖咖啡、是否还常常熬夜。未待我回答,他便细细叮嘱道:“少饮些咖啡,多锻炼身体。另外,论文要抓紧开始规划和写作了,像你师兄师姐那般,‘前头赶得紧些,后头便从容了’。”
就这样,我们在导师的带领下,慢悠悠地走着,恰巧路过一家校内咖啡馆,眼瞅着还未打烊,导师便领着大家一同吃个夜宵。我们喝着奶茶,吃着蛋糕;导师时而引经据典,时而妙语连珠;师兄师姐们聊起近日趣闻,言语间妙趣横生。师门此起彼伏的笑声在咖啡店暖黄的灯光里荡漾开来。
咖啡馆要打烊了,我们一群人沿着来时的小径踱步出来,桂香如来时般依旧,我们的心头却装满了来时所没有的暖意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行至图书馆前的广场,路灯将我们的身影拉得修长。我们与导师互道珍重,他站在光晕里目送我们,而后,我们便三三两两地散去了。
待我转身回望,师兄、师姐的身影早已没入夜色,唯有那桂花香还在原地徘徊。
如此闲适、美好的一夜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当日导师挂念着的一群可爱的人儿呀,自那日后,便转身奔向各处——师兄穿梭于各地档案馆,埋首故纸堆中查证史料;师姐辗转各地考场,奋力搏取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转眼间,师兄师姐均已各奔前程。未及回神,我也踏入兵荒马乱的毕业季。
三年忽逝,如今我已赴他乡继续深造,导师的朋友圈里也时常有新面孔。又是一年金秋九月,手机推送的消息提醒着我:南大的桂花又开了。只是不知那同样的桂花树下,是否又有一群年轻的学子,正凝神聆听导师的谆谆教诲。
如今忆来,那个秋夜里,年轻的我们怀揣着各自的烦恼,在氤氲桂香中惺惺相惜地交换着彼此的不安与迷茫。三年后,我立于时光的彼岸回望,恨不能穿越回三年前,我多想告诉那时为论文焦头烂额的师兄:他的论文顺利发表了,读博之旅甚是顺利。我多想安慰当年为求职焦虑、失眠的师姐:她果真等到了最适合她的工作,能够在喜欢的岗位上闪闪发光,江南烟雨润泽着街巷,也悄然润泽着她所有的疲惫。我更想告诉我的导师:您当年牵挂的小徒弟,毕业后几经辗转,对未来的规划逐渐清晰,也终于领悟到那个秋夜导师的每句叮嘱背后的深意。
千年前的某个中秋夜,诗人王建独立于中庭,望见桂影婆娑,怅然吟道: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韶光易逝,风流云散,但花信不改,岁岁依旧。千年之后我在他乡望见同一轮明月,可那被冷露浸湿的,又何止是桂花?更是我心底泛起的三重思念:一重念南大满校园的氤氲桂香,二重念导师昔日的谆谆嘱咐,三重念那年秋夜共醉花香的每一个人。
(转载自《av片 报》2025年第26期,作者陈宣谕,av片 2024届硕士毕业生,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)